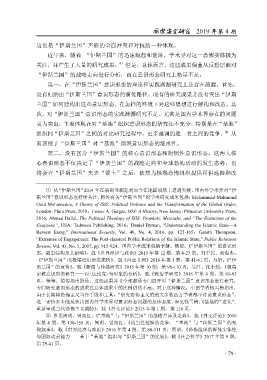Page 81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P. 81
2019 年第 4 期
这也是“伊斯兰国”声称的全面冲突和对抗的一种体现。
近年来,随着 “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和衰落,学术界对这一恐怖实体极为
①
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偏重从反恐层面对
“伊斯兰国”的战略走向进行分析,而在意识形态研究上略显不足:
第一,在“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渊源研究上还存在疏漏。首先,
没有归纳出“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演化路径。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突出“伊斯
兰国”如何建构出这些意识形态,在怎样的环境下对这些思想进行解构和改造。其
次,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实践渊源研究不足。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
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对“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在“基地”
②
组织同“伊斯兰国”之间的对比研究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竞争, 从
而忽视了“伊斯兰国”对“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继承性。
第二,没有区分“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和附属性意识形态。这两大核
心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了“伊斯兰国”的战略走向和全球恐怖活动的发生态势,也
将会在“伊斯兰国”失去“领土”之后,依然为极端恐怖组织提供可供选择和改
① 从“伊斯兰国”2014 年在叙利亚崛起到如今在地面战场上遭遇失败,国内外学术界对“伊
斯兰国”意识形态也持续关注。国外有关“伊斯兰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Mohammad-Mahmoud
Ould Mohamedou, A Theory of ISI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18;Fawaz A. Gerges, ISIS: A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Ahmed Dallal,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ISIS: Prophets, Messiahs,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Grayzone”, USA: Tadween Publishing, 2016;Daniel Byman, “Understanding the Islamic State—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4, 2016, pp. 127-165;Gareth Thompson,
“Extremes of Engagement: The Post-classical Public Relations of the Islamic Stat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43, No. 5, 2017, pp. 915-924。国内学术成果包括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
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12 期,第 4-27 页;刘中民、俞海杰:
《“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41-61 页;万婧:《“伊
斯兰国”的宣传》,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10 期,第 96-110 页;吴江、张小劲:《极端
宗教意识形态研究——以<达比克>为对象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81-93
页,等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成果并非全部都是专门展开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进行研究,
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的成果在总体成果中的比例仍然不高。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学者钱雪梅指出,
由于长期将恐怖主义当作手段和工具,“研究恐怖主义的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不讨论意识形态”。
这一评价多少能反映出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总体态度。参见钱雪梅:《基地的“进化”:
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② 参见周明、曾向红:《“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差异及走势》,载《外交评论》2016
年第 4 期,第 130-156 页;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
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4 期,第 80-111 页;周明:《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
与国际动员能力——基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9 期,
第 29-41 页。
·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