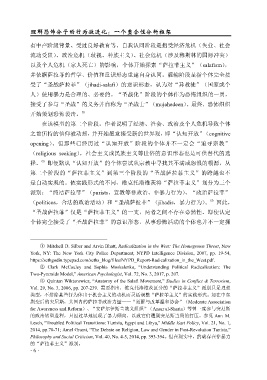Page 8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P. 8
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有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等。自我认同阶段是指受经济危机(失业、社会
流动受阻)、政治危机(歧视、种族主义)、社会危机(涉及穆斯林的国际冲突)
以及个人危机(家人死亡)的影响,个体开始探索“萨拉菲主义”(salafism),
并依据萨拉菲的哲学、价值和意识形态重建自身认同。灌输阶段是指个体完全接
受了“圣战萨拉菲”(jihadi-salafi)的意识形态,认为对“异教徒”(国家或个
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必要的。“圣战化”阶段的个体作为恐怖组织的一员,
接受了参与“圣战”的义务并自称为“圣战士”(mujahedeen)。最终,恐怖组织
①
开始策划恐怖袭击。
在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作者说明了经济、社会、政治及个人危机导致个体
之前所持的信仰被动摇,并开始愿意接受新的世界观,即“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但那些已经历过“认知开放”阶段的个体并不一定会“追寻宗教”
(religious seeking),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等世俗的意识形态也是可供替代的选
②
择。 即便默认“认知开放”的个体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源,从
第二个阶段的“萨拉菲主义”到第三个阶段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的跨越也不
是自动实现的。依实践形式的不同,维克托洛维茨将“萨拉菲主义”划分为三个
派别:“纯洁萨拉菲”(purists,宣教等非政治、非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
③
(politicos,合法的政治活动)和“圣战萨拉菲”(jihadis,暴力行为)。 因此,
“圣战萨拉菲”仅是“萨拉菲主义”的一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即使认定
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的意识形态,从事恐怖活动的个体也并不一定拥
① Mitchell D. Silber and Arvin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New
York, NY: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Intelligence Division, 2007, pp. 19-54,
https://sethgodin.typepad.com/seths_blog/files/NYPD_Report-Radicalization_in_the_West.pdf.
②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 207.
③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 需要指出,维克托洛维茨区分的“萨拉菲主义”派别只是理想
类型,不排除某些行为体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而灵活调整“萨拉菲主义”的实践形式。如在中东
剧变后的突尼斯,其国内的萨拉菲政治力量——“觉醒与改革温和协会”(Moderate Association
for Awareness and Reform)、“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Sharia)等曾一度参与突尼斯
的政治转型进程,只因过早地展现了暴力倾向,以致它们遭到突尼斯当局的打压。参见 Ann M.
Lesch, “Troubled Political Transitions: Tunisia, Egypt and Liby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1,
2014, pp.70-71; Amel Grami, “The Debate on Religion, Law and Gender in Post-Revolution Tunisia,”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40, No. 4-5, 2014, pp. 393-394。但在现实中,的确存在非暴力
的“萨拉菲主义”派别。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