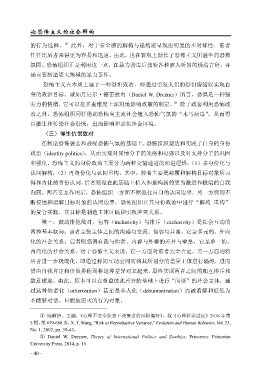Page 42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P. 42
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①
的行为选择。 此外,对于安全感的解构与建构还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
往往比后者来得更为容易和迅速。由此,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恐怖主义所滋生的恐怖
氛围。恐怖组织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暴力袭击后鼓噪各种骇人听闻的极端言辞,并
扬言要制造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恐惧政治,即通过引发人们的恐惧情绪以实现自
身的政治目标。诚如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所言,恐惧是一种强
②
有力的情绪,它可以在多重维度上深刻地影响政策的制定。 除了政客利用恐怖政
治之外,恐怖组织同样借助恐怖向主流社会植入恐怖气氛的“木马病毒”,从而得
以催生和传染社会恐慌,进而影响和恶化社会环境。
(三)催生仇恨敌对
在制造恐怖袭击和鼓噪恐怖气氛的基础上,恐怖组织塑造和实践了自身的身份
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从而实现对同情分子的笼络和蛊惑以及对支持分子的巩固
和强化。恐怖主义的身份政治主要分为两种交错递进的演进逻辑:(1)去身份化与
认同解构;(2)再身份化与认同重构。其中,前者主要是颠覆和解构目标对象所习
得和内化的身份认同,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植入和重构新的更为激进和极端的自我
归属。两者交互作用后,恐怖组织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的认同边界,另一方面则不
断侵蚀和消解目标对象的认同边界。恐怖组织在其身份政治中进行“解构-重构”
的复合实践,其目标是制造主体区隔和引致冲突关系。
第一,鼓动排他敌对。包容(inclusivity)与排斥(exclusivity)是社会互动的
两种基本取向:前者主张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包容与并蓄,它是多元的、外向
化的社会关系;后者则强调自我与他者、内群与外群的差异与壁垒,它是单一的、
内向化的社会关系。对于恐怖主义来说,它一方面对前者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则将
后者进一步极端化,即通过封闭互动空间而将其所划分的差异主体进行隔绝,进而
借由自我肯定和价值排他而将这种差异对立起来,最终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排斥和
敌意螺旋。由此,原本可以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进行“间谈”的社会主体,通
过这种他者化(otherization)甚至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而被消解和贬低为
不能够对话、只能被消灭的行为对象。
① 陆静怡、王越:《心理不安全状态下决策者的风险偏好》,载《心理科学进展》2016 年第
5 期,第 679-680 页;X. T. Wang, “Risk as Reproductive Varian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3,
No. 1, 2002, pp. 39-43。
② Daniel W. Drezn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Zomb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6.
·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