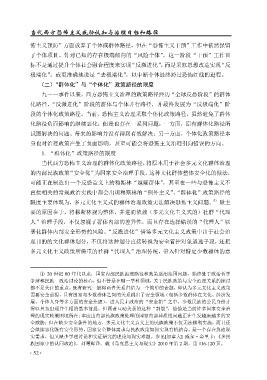Page 54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P. 54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怖主义预防”方面放弃了个体或群体路径,但在“恐怖主义干预”工作中依然保留
了个体项目。针对已知的存在极端倾向的“风险个体”,这一阶段“干预”工作目
标不是通过提升个体社会融合程度来实现“反激进化”,而是采取思想改造实现“反
极端化”,或更准确地说是“去极端化”,以中断个体最终跨过恐怖红线的进程。
(二)“群体化”与“个体化”政策路径的限度
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政策路径经历“全球反恐阶段”的群体
化路径、“反激进化”阶段的群体与个体并行路径,并最终发展为“反极端化”阶
段的个体化政策路径。当前,恐怖主义治理采取个体化政策路径,虽然避免了群体
化路径负面影响的继续恶化,但是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原有群体化路径所
试图解决的问题、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个体化政策路径本
身也对治理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将恐怖主义治理引向错误的方向。
1. “群体化”政策路径的限度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群体化政策路径,将原本用于社会多元文化群体治理
的内部民族政策“安全化”为国家安全治理手段。这种文化群体整体安全化的做法,
可能正在制造出一个反恐意义上的穆斯林“嫌疑群体”,甚至在一些与恐怖主义不
直接相关的常规政治实践中都会出现穆斯林的“例外主义”。“群体化”政策路径的
①
限度主要体现为,多元文化主义式的群体治理政策无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最主
要的原因在于,将穆斯林视为整体,并进而依赖(多元文化主义式的)社群“代理
人”治理手段,不仅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而且存在选择错误的“代理人”以
恶化群体内部安全形势的风险。“反激进化”借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出于社会治
理目的的文化群体划分,不仅将这种划分直接转换为安全管控对象遴选手段,还把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倚重的社群“代理人”治理传统,带入针对特定少数群体的意
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内部民族治理路径和政策适用范围问题,始终处于政治哲学
争辩和民族—政治讨论的核心,但不管是在哪一学科领域,关于民族政策与安全治理关系的探讨
都不是关注的重点。既有研究一般将两者关系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命题,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需要安全前提,只有国家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关系跳出了安全领域(包括少数群体在文化、经济发
展、个体人身等多方面的安全焦虑),进入民主政治的“安全箱”之中,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才
得以具备出现并生根的基本前提。但两者互动关系的这种“割裂”,恰恰是当前许多国家安全治
理的现实政策困境所在:本应由内部民族政策处理的国家内部异质性问题正在生发越来越多的安
全威胁;但在缺少安全条件的地方,多元文化主义意义上的民族政策不仅无法顺利实施,而且还
会继续恶化既有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整体需求与民族政策如何实现有机结合,是一个存在急迫现
实需求、但又缺少学理讨论和实证研究的理论与现实难题。参见[加拿大] 威尔·金里卡:《多民
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刘曙辉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 2 期,第 116-120 页。
·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