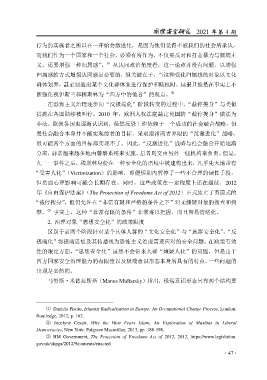Page 49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P. 49
2021 年第 4 期
行为的实施者之所以在一开始会激进化,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被我们的社会所承认,
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必须有所作为,不仅要反对和打击暴力与极端主
①
义,还要增强一种归属感”。 从认同政治角度看,这一论点并没有问题,以增强
归属感的方式增强认同感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当这种强化归属感的对象以文化
群体划界,甚至制造出某个文化群体来进行保护和赋权时,结果只能是在事实上不
②
断强化视伊斯兰和穆斯林为“西方中的他者”的观点。
在恐怖主义治理逐步向“反极端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截停搜身”与类似
措施在各国陆续被叫停。2010 年,欧洲人权法庭裁定英国的“截停搜身”做法为
非法。欧洲各国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反恐工作依赖于一个成功的社会融合战略,但
是社会融合本身并不能实现前者的目标,采取混淆两者界限的“反激进化”战略,
很可能两个方面的目标都实现不了。因此,“反激进化”战略与社会融合开始逐渐
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由警察系统来实施,后者则交由另外一些机构来负责。但是,
九一一事件之后,穆斯林身份在一种安全化的语境中被建构出来,几乎先天地带有
“受害人化”(Victimization)的影响,即便短期内暂停了一些不合理的硬性手段,
但负面心理影响可能会长期存在。同时,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在继续,2012
年《自由保护法案》(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 of 2012)正式废止了英国式的
“截停搜身”,但仍允许在“非常有限和严格的条件之下”对无嫌疑对象的搜查和拘
③
禁。 事实上,这种“非常有限的条件”非常难以把握,而且容易情绪化。
2. 治理对象“思想安全化”的政策限度
区别于前两个阶段针对某个具体人群的“文化安全化”与“族群安全化”,“反
极端化”将极端思想及其传播视为恐怖主义治理需要应对的安全问题。在政策有效
性的限定方面,“思想安全化”虽然不会带来人群“嫌疑人化”的问题,但是由于
西方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极端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一些问题的
出现是必然的。
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Midlarsky)指出,极端意识形态具有两个结构要
① Daniela Pisoiu, Islamist Radicalisation in Europe: An Occupational Change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162.
② Jocelyne Cesari, Why the West Fears Islam: An Exploration of Muslim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88-198.
③ HM Government,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 of 2012, 2012, https://www.legislation.
gov.uk/ukpga/2012/9/contents/enacted.
·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