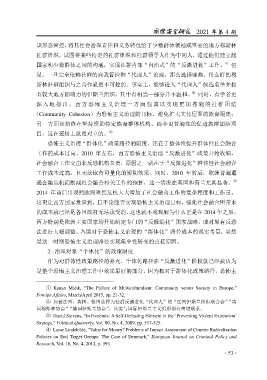Page 55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P. 55
2021 年第 4 期
识形态管控,将其社会治理责任和义务转包给了少数群体领袖或重要的地方穆斯林
社群组织,试图将某些特定的社群组织和社群领导人作为中间人,通过他们建立起
①
国家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沟通,实现社群内部“自治式”的“反激进化”工作。 但
是,一旦完全依赖社群的自我管控和“代理人”治理,那么选择哪些、什么样的穆
斯林社群组织与之合作就是不可控的。事实上,能够进入“代理人”候选名单并拥
②
有较大地方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温和。 同时,有学者更
深入地指出,西方恐怖主义治理一方面强调以实现更加普遍的社群团 结
(Community Cohesion)为恐怖主义治理的目标,避免扩大文化层面的族裔隔离;
另一方面却始终在坚持资助特定族裔群体机构、而非更普遍性的促进族群团结项
③
目,这在逻辑上就是对立的。
恐怖主义治理“群体化”政策路径的限度,还在于整体性提升群体性社会融合
工作的成本过高。2010 年左右,西方恐怖主义治理“反激进化”政策开始收缩,
社会融合工作交由非反恐机构负责,原因之一就在于“反激进化”群体性社会融合
工作成本过高,且无法取得可量化的短期效果。同时,2010 年前后,欧洲普遍遭
④
遇金融危机而削减社会融合相关工作的预算,这一情况在英国和荷兰尤其显著。
2014 年前后出现的欧洲难民危机大大增加了社会融合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工作量。
这更让西方国家意识到,且不论能否实现恐怖主义治理目标,强化社会融合所带来
的成本就已经是各国政府无法承受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 2014 年之后,
西方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均开始制定专门的“反极端化”国家战略,或对原有反恐
法进行大幅调整。各国对于恐怖主义治理的“群体化”路径成本的现实考量,显然
是这一时期恐怖主义治理路径实现集中性转变的直接原因。
2. 治理对象“个体化”的政策限度
作为对群体性政策路径的补充,个体化路径在“反激进化”阶段就已经被认为
是整个恐怖主义治理工作中效果最好的部分。因为相对于群体化政策路径,恐怖主
① Kenan Malik, “The Failure of Multiculturalism: Community versus Society i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 pp. 21-32.
② 如被法国、英国、德国选择为社群反激进化“代理人”的“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英
国穆斯林协会”“德国伊斯兰协会”,其实与国际伊斯兰主义组织都有密切联系。
③ David Stevens, “In Extremis: A Self-Defeating Element in the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Strategy,”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80, No. 4, 2009, pp. 517-525.
④ Lasse Lindekilde, “Value for Money? Problems of Impact Assessment of Counter-Radicalisation
Policies on End Target Groups: The Case of Denmark,”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Vol. 18, No. 4, 2012, p. 393.
·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