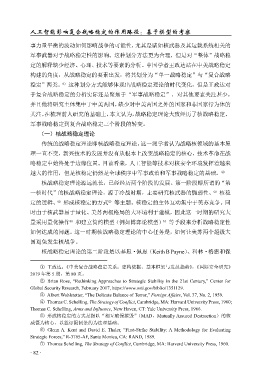Page 84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P. 84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事力量平衡的波动如何影响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诸如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相关的
军事武器对于战略稳定性的影响。这种划分方法更为合理,但是对“整体”战略稳
定的解释缺少经济、心理、技术等要素的分析。中国学者王政达站在中美战略稳定
构建的角度,从战略稳定的要素出发,将其划分为“单一战略稳定”与“复合战略
①
稳定”两类。 这种划分方式能够体现出战略稳定理论的时代变化,但是王政达对
于复合战略稳定的分析实际还是聚焦于“军事战略稳定”,对其他要素关注甚少,
并且他将研究主体集中于中美两国,缺少对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
关注。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战略稳定理论大致经历了核战略稳定、
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三个阶段的转变。
(一)核战略稳定理论
传统的战略稳定理论即核战略稳定理论。这一派学者认为战略核领域的基本原
理一直不变,新兴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略稳定的核心,技术革命在战
略稳定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目前看来,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核安全环境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但是核稳定仍然是全球秩序中军事政治和军事战略稳定的基础。
②
核战略稳定理论源远流长,已经经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即所谓的“第
一核时代”的核战略稳定理论,源于冷战时期,主要研究核武器的脆弱性、 核稳
③
定的逻辑、 形成核稳定的方式 等主题。核稳定的主体互动集中于美苏竞争。同
⑤
④
时由于核武器易于量化、美苏两极格局的大环境利于建模,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大
量采用量化操作 和建立简约模型(例如博弈论模型) 等手段来分析战略稳定性
⑦
⑥
如何达成的问题。这一时期核战略稳定理论的中心任务是,如何让美苏两个超级大
国避免发生核战争。
核战略稳定理论的第二阶段是以基思·佩恩(Keith B Payne)、科林·格雷和保
① 王政达:《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国际安全研究》
2019 年第 5 期,第 80 页。
② Brian Rose, “Rethinking Approaches to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enter for
Global Security Rrsearch, February 2017, https://www.osti.gov/biblio/1351129.
③ Albert Wohlstetter,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Vol. 37, No. 2, 1959.
④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⑤ 形成核稳定的方式是指以“相互确保摧毁”(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核
威慑为核心,以签订限制条约为法理基础。
⑥ Glenn A. Kent and David E. Thaler, “First-Strike Stability: A Methodology for Evaluating
Strategic Forces,” R-3765-AF, Santa Monica, CA: RAND, 1989.
⑦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