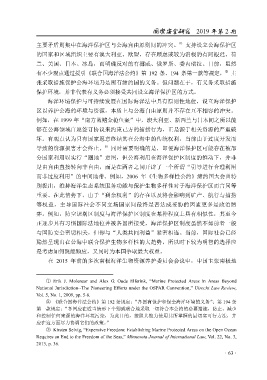Page 66 - 201902
P. 66
2019 年第 2 期
①
主要矛盾则集中在海洋保护区与公海自由原则间的冲突。 支持设立公海保护区
的国家和区域组织主要有澳大利亚、欧盟,存在顾虑或较为消极的有阿根廷、荷
兰、美国、日本、冰岛,而明确反对的有挪威、俄罗斯、委内瑞拉。目前,虽然
②
有不少观点通过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92 条、194 条第一款等规定, 主
张采取措施保护公海环境乃是所有缔约国的义务。但问题在于,有义务采取措施
保护环境,并非代表有义务必须接受共同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方式。
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海洋法中具有原则性地位,设立海洋保护
区以养护公海的环境与资源,本质上与公海自由原则并不存在互不相容的冲突。
例如,在 1999 年“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中,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日本间之所以能
够在公海领域自愿签订协议来约束己方的捕捞行为,正是源于相关资源的严重破
坏。有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愿意终结其在公海中的传统权利,当前由于过度开发而
③
导致的资源损害才会终止。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即便海洋保护区可能存在被部
分国家利用以实行“圈地”意图,但公海利用在海洋保护区制度的推动下,并非
是由自由直接转向非自由,而是在两者之间开辟了一个所谓“引导进行合理利用
而非过度利用”的中间地带。例如,2006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曾特
别提出,维持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海洋保护区而言同等
重要。在此情势下,由于“剩余权利”的存在以及将会影响到矿产、航行与捕捞
等权益,主导国际社会不同立场国家间最终是否达成妥协的因素更多是政治博
弈。例如,防空识别区制度与海洋保护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其至今
正逐步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并被各国所接受,海洋保护区制度虽然不如前者一般
与国防安全密切相关,但却与“人类共同利益”紧密相连。当前,国际社会已经
隐然呈现出在公海中联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趋势,所以时下较为明智的选择应
是考虑如何既能顺应,又同时为本国争取最大权益。
在 2015 年前的多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会议中,中国主张南极地
① Erik J. Molenaar and Alex G. Oude Elferink,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The Pioneering Efforts under the OSPAR Convention,” Utrecht Law Review,
Vol. 5, No. 1, 2009, pp. 5-6.
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92 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第 194 条
第一款规定:“各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
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为此目的,按照其能力使用其所掌握的最切实可行方法,并
应在这方面尽力协调它们的政策。”
③ Kirsten Selvig, “Expensive Freedom: Establish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the Open Ocean
Requires an End to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No. 3,
2013, p. 36.
·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