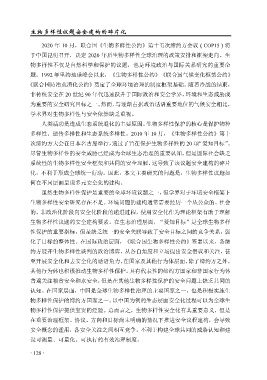Page 130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P. 130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2020 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将
于中国昆明召开,决定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政策安排和框架走向。生
物多样性不仅是自然科学和保护的议题,也是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命
题。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以来,《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框架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
非传统安全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迅速跃升于国际政治和安全学界,环境和生态威胁成
为重要的安全研究目标之一。然而,与逐渐占据政治话语重要地位的气候安全相比,
学术界对生物多样性与安全依然缺乏重视。
人类活动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是保护物种
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2010 年 10 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通过了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20 项“爱知目标”。
尽管生物多样性的安全威胁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认知,但是国际社会缺乏
系统性的生物多样性安全框架和共同的安全理解,这导致了该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
化,不利于形成全球统一行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议题如
何在不同层面呈现多元安全化的建构。
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重要的全球环境议题之一,但学界对于环境安全框架下
生物多样性安全研究存在不足。环境问题的建构通常需要经历一个从公众的、社会
的、非政治化阶段向安全化阶段的递进过程,使用安全化作为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
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安全建构要素。在生态治理层面,“爱知目标”是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重要指标,但是缺乏统一的安全关联导致了安全目标之间的竞争关系,弱
化了目标的整体性。在国际政治层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以来,各缔
约方展开生物多样性谈判的政治博弈,从各自角度和立场提出安全倡议和关注,甚
至开展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话语角力。在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层面,除了缔约方之外,
其他行为体也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代表性的缔约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普遍关注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但是在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安全问题上缺乏共同的
认知。在国家层面,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主要国家之一,也是积极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缔约方国家之一。以中国为例的生态层面安全化过程可以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宝贵的经验。总而言之,生物多样性安全化有其重要意义,但是
在重要治理框架、协议、方向和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推进安全议程建构,会导致
安全概念的滥用,各安全关注之间相互竞争,不利于构建全球共同的威胁认知和建
设可测量、可量化、可执行的有效治理制度。
·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