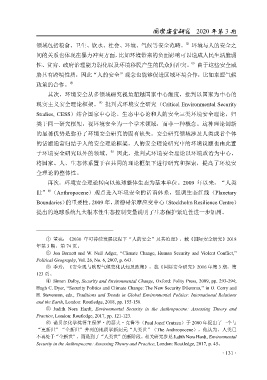Page 13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P. 133
2020 年第 3 期
①
领域包括粮食、卫生、饮水、社会、环境、气候等安全范畴。 环境与人的安全之
间的关系也体现在暴力冲突方面,比如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造成人民生活脆弱
②
性、贫穷、政府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环境移民产生的民众间冲突。 由于这些安全威
胁具有跨境性质,因此“人的安全”观念也能够促进区域环境合作,比如东盟气候
政策的合作。
③
其次,环境安全从多领域研究视角超越国家中心维度,批判以国家为中心的
④
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框架。 批判式环境安全研究(Critic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tudies, CESS)结合国家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和人的安全三类环境安全理论,归
类于同一研究框架,视环境安全为一个学术领域,而非一种概念。这种理论创新
的显著优势是弥补了环境安全研究的固有缺失。安全研究领域涉及人类或者个体
的话题通常归结于人的安全理论框架,人的安全理论研究中的环境议题也由此置
⑤
于环境安全研究以外的领域。 因此,批判式环境安全理论以环境政治为中心,
将国家、人、生态体系置于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和探索,提高了环境安
全理论的整体性。
再次,环境安全理论转向以地球整体生态为基本单位。2009 年以来,“人类
世” (Anthropocene)观点进入环境安全的话语体系,强调生态红线(Planetary
⑥
Boundaries)的重要性。2009 年,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提出的地球系统九大根本性生态控制变量说明了生态保护紧迫性进一步加剧。
① 董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74 页。
② Jon Barnett and W. Neil Adger, ‘‘Climate Change, Human Security and Violent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6, No. 6, 2007, p. 643.
③ 季玲:《安全观与欧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123 页。
④ Simon Dalb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Oxford: Polity Press, 2009, pp. 293-294;
Hugh C. Dyer, ‘‘Security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New Security Dilemma,’’ in O. Corry and
H. Stevenson, eds., Traditions and Trend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arth,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155-156.
⑤ Judith Nora Hardt,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Anthropocene: Asses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21-123.
⑥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约瑟夫·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于 2000 年提出了一个与
“更新世”“全新世”并列的地质学新纪元“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他认为,人类已
不再处于“全新世”,而是到了“人类世”的新阶段。相关研究参见 Judith Nora Hardt,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Anthropocene: Asses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45。
·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