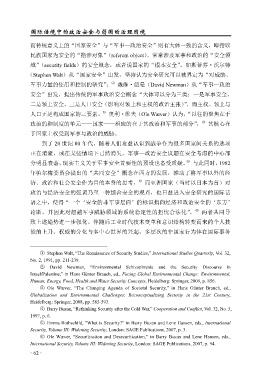Page 64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P. 64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政治安全”则有大体一致的含义,即指以
民族国家为安全的“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常常涉及军事和政治的“安全领
域”(security fields)的安全概念,或者说国家的“根本安全”。如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从“国家安全”出发,坚持认为安全研究可以被界定为“对威胁、
①
军事力量的使用和控制的研究”; 戴维·纽曼(David Newman)从“军事—政治
安全”出发,提出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概念“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军事安全,
二是领土安全,三是人口安全(影响对领土和主权的政治主张)”,而主权、领土与
②
人口正是构成国家的三要素。 奥利·维夫(Ole Wæver)认为,“以往的聚焦在于
③
政治的和制度的单元——国家——相应的在于其政治和军事的部分”, 其核心在
于国家主权受到军事与政治的威胁。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人们愈益认识到战争作为很多国家间关系的选项
正在消逝,或在某些情境下已然消失,军事—政治安全议题在安全考虑的中心部
④
分明显衰落,现实主义关于军事安全首要性的预设也备受质疑。 与此同时,1982
年帕尔梅委员会提出的“共同安全”概念在西方的发展,推动了将军事以外的经
⑤
济、政治和社会安全作为目的本身的思考, 而亚洲国家(当时以日本为首)对
政治与经济安全的强调乃至一种综合安全的观点,也日益进入安全研究的国际话
语之中,使得“一个‘安全的非军事层面’的标识指向经济和政治安全的‘东方’
论断,并因此对超越军事威胁领域的系统稳定性的担忧合法化”, 两者共同导
⑥
致上述趋势进一步强化。伴随后工业时代技术变革和意识结构转变而来的个人技
能的上升、权威的分化与多中心世界的兴起,多层次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
① Stephen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2, 1991, pp. 211-239.
② David Newman, “Environmental Schizophrenia and the Security Discourse in
Israel/Palestine,”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Fa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nvironmental,
Human, Energy, Food, Health and Water Security Concepts,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p. 856.
③ Ole Wæver, “The Changing Agenda of Societal Security,”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Re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p. 585-593.
④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2, No. 5,
1997, p. 6.
⑤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III: Widening Secur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3.
⑥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III: Widening Secur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94.
·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