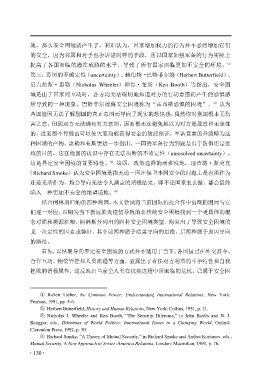Page 13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P. 132
ၹ൝০֝ğ߄ࢳ٤Ԯνಆ֥תૐਫ਼ࣥ
地,那么安全困境就产生了。利珀认为,国家增加权力的行为并不必然增加它们
的安全,因为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所以国家加强军备的行为实际上
提高了各国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导致了所有国家面临更加不安全的环境。
①
第三,意图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和肯·布斯(Ken Booth)等指出,安全困
境是由于国家间互动时,各方均无法确切地知道对方的行动意图而产生的恐惧感
②
所导致的一种现象。巴特菲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恐惧的困境”, 认为
各国皆因无法了解别国的真正意图而导向了现实的恐惧感,虽然你对别国根本无伤
害之意,但因双方无法确知对方意图,因而都无法避免地以为对方是敌意和无理性
的,进而都不肯做出可以使大家均能获得安全的彼此保证,军备竞赛的升级即为这
种困境的产物。惠勒和布斯更进一步指出,一国的军备行为到底是出于防御还是进
攻的目的,这在他国的认识中存在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ed uncertainty),
③
这是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第四,政策选择的两难境地。理查德·斯莫克
(Richard Smoke)认为安全困境是指无论一国在保卫本国安全的问题上是有所作为
还是无所作为,均会导向无法令人满意的消极结果,即不论国家怎么做,都会最终
陷入一种更加不安全的绝望境地。
④
结合柯林斯归纳的四种溯因,本文尝试将当前国际抗疫合作中出现的困局与它
们逐一对应,以期为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非传统安全困境找到一个更具体的概
念对照和溯源框架。柯林斯分列出的四种安全困境类型,均突出了导致安全困境的
某一决定性的因素或特征,其中前两种属于结果导向的思维,后两种属于原因导向
的路径。
首先,以结果导向界定安全困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当下。各国虽已在外交辞令、
合作互动、物资管控和人员流通等方面,显露出了有损对方利益的斗争特性和自我
挫败的消极属性,这反映出当前全人类在抗疫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已属于安全困
① Robert Lieber, No Common Powe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earson, 1991, pp. 5-6.
②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lins, 1951, p. 21.
③ Nicholas J. Wheeler and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is and N. J.
Rengger, eds.,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30.
④ Richard Smoke, “A Theory of Mutual Security,” in Richard Smoke and Andrei Kortunov, eds.,
Mutual Security: A New Approach to Soviet -America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p. 76.
· 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