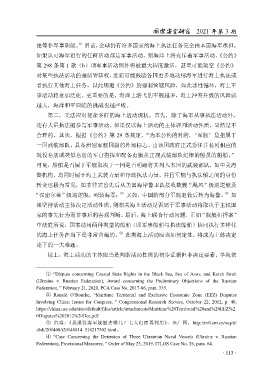Page 115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
P. 115
2021 年第 3 期
①
建等非军事职能。 目前,全球仍有许多国家的海上执法任务完全由本国海军承担,
如果认可海军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军事活动,则海洋上将充斥着军事活动,《公约》
第 298 条第 1 款(b)项军事活动例外将被最大程度激活,甚至可能架空《公约》
对某些执法活动的强制管辖权,进而可能鼓励各国更多地动用海军进行海上执法或
者执行其他海上任务,以此规避《公约》的强制管辖风险,如此恶性循环,海上军
事活动将愈加泛化。更重要的是,海洋上游弋的军舰越多,海上冲突升级的风险就
越大,海洋和平面临的挑战也越严峻。
第二,无法应对复杂多样的海上活动现状。首先,除了海军从事执法活动外,
还有大量执法船参与军事活动。如果仅以海上活动的主体评判活动性质,显然是不
合理的。其次,根据《公约》第 29 条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军舰’是指属于
一国武装部队、具备辨别军舰国籍的外部标志、由该国政府正式委任并名列相应的
现役名册或类似名册的军官指挥和配备有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纪律的船员的船舶。”
可见,船舶是否属于军舰取决于一国是否明确将其列入本国的武装部队,如中美海
警机构,均同时属于海上武装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并且军舰与执法船之间的身份
转变也极为常见,如菲律宾曾先后从美国海岸警卫队接收数艘“飓风”级巡逻艇及
③
②
“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列装海军; 又如,中国的部分军舰退役后转为海警。 如
果坚持活动主体决定活动性质,则相关海上活动是否属于军事活动将取决于主权国
家的事先行为而非事后的客观判断。最后,海上联合行动问题,正如“舰艇扣押案”
中法庭所说,国家动用两种类型的船舶(即军事船舶与执法船舶)协同执行多样化
④
的海上任务在当下是非常普遍的。 此类海上活动应当如何定性,将成为主体决定
论下的一大难题。
综上,海上活动的主体应当是判断活动性质的初步证据但非决定要素。单纯依
① “Dispute concerning Coastal State Rights in the Black Sea, Sea of Azov, and Kerch Strait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Award concerning the Preliminary Obj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February 21, 2020, PCA Case No. 2017-06, para. 335.
② Ronald O’Rourke, “Maritime Territorial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Disputes
Involving China: Issues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2, 2012, p. 40,
https://china.usc.edu/sites/default/files/article/attachments/Maritime%20Territorial%20and%20EEZ%2
0Disputes%202012%20Dec.pdf.
③ 危瑶:《我退役海军舰艇去哪儿?七大归宿再利用》,央广网,http://mil.cnr.cn/wqzb/
zbdt/201408/t20140814_516217502.html。
④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ovisional Measures, ” Order of May 25, 2019, ITLOS Case No. 26, para. 64.
·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