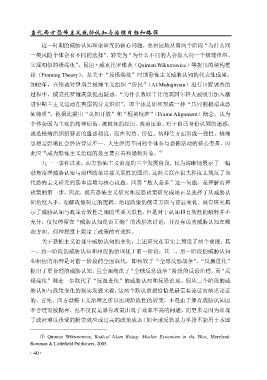Page 4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P. 42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这一时期的威胁认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相应地从前两个阶段“为什么同
一类风险个体会有不同的选择”,转变为“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加入同一个极端组织、
实现相似的极端化”。昆坦·威克托罗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等提出的架构理
论(Framing Theory),是关于“反极端化”时期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代表性成果。
2002年,在伦敦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侨民”(Al-Muhajiroun)进行田野调查的
过程中,威克托罗维茨就提出疑惑,“为什么数以千计的英国年轻人被吸引加入激
进伊斯兰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分支组织”,即个体是如何形成一种“共同的极端或恐
怖特质”。他据此提出“认知开放”和“框架校准”(Frame Alignment)概念,认为
个体会因为主观的精神痛苦、被歧视的经历、政治压迫、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迷惑,
或是极端组织招募者的蛊惑劝说,而在利益、价值、信仰等方面形成一致性。极端
思想是影响社会经济背景不一、人生经历不同的个体参与恐怖活动的核心变量,因
①
此应当成为恐怖主义治理的最主要打击和遏制对象。
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一幅
恐怖治理威胁认知与治理政策直接关联性的图谱,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当
代恐怖主义研究的基本语境与核心议题。回答“敌人是谁”这一问题,是理解治理
政策的第一步,因此,既有恐怖主义研究和反恐政策研究成果正是选择了从威胁认
知角度入手,理解政策制定的逻辑、治理政策的侧重方面与前后变化。既有研究揭
示了威胁认知与政策有效性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但是对于认知和有效性的解释并不
充分,仅仅停留在“威胁认知是否正确”的浅层次讨论,并没有说明威胁认知在哪
些方面、何种程度上限定了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恐怖主义治理中威胁认知的变化,上述研究在事实上预设了两个前提:其
一,后一阶段的威胁认知和相应的治理优于前一阶段;其二,后一阶段的威胁认知
和相应的治理是对前一阶段的全面取代,即相较于“全球反恐战争”,“反激进化”
提出了更合理的威胁认知,且全面淘汰了“全球反恐战争”阶段的反恐治理,而“反
极端化”则进一步取代了“反激进化”的威胁认知和反恐治理。但从三个阶段的威
胁认知与政策变化的现实发展来看,这两个默认前提恰恰是最需要论证而缺乏论证
的。首先,西方恐怖主义治理之所以出现阶段性的转变,不是由于原有威胁认知因
不合理而被抛弃,也不仅仅是原有政策出现了效率不高的问题,而更多是因为出现
了政府难以承受的附带效应或过高的政策成本(如全球反恐暴力手段不能用于本国
① Quintan Wiktorowicz, Radical Islam Rising: Muslim Extremism in the West,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