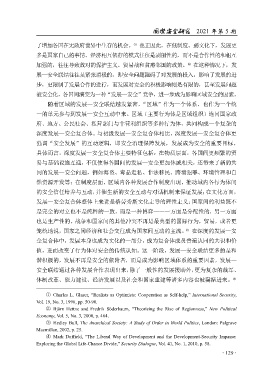Page 13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5期
P. 131
2021 年第 5 期
了增加各国在无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机会。 也正因此,在低制度、弱文化下,发展更
①
多是国家自己的事情,经济相互依存的模式往往是剥削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和相互
加强的,往往导致敌对的保护主义、贸易战和贫瘠邻国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发
②
展—安全联结往往是紧张消极的,即安全问题阻碍了对发展的投入,影响了发展的进
步,更限制了发展合作的进行,而发展对安全的积极影响则是有限的,甚至发展问题
被安全化,各国间演变为一种“发展—安全”竞争,进一步成为影响区域安全的因素。
随着区域的发展—安全联结越发紧密,“区域”作为一个体系,也作为一个统
一的单元参与到发展—安全互动中来。区域(主要行为体是区域组织)连同国家政
府、地方、公民社会、私营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等多种行为体,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
深度发展—安全复合体。与初级发展—安全复合体相比,深度发展—安全复合体更
强调“安全发展”的互动逻辑,即安全治理保障发展,发展成为安全的重要目标。
具体而言,深度发展—安全复合体主要特征包括:在物质层面,各国间更频繁的贸
易与基础设施互通,不仅使得各国间的发展—安全更加休戚相关,还带来了新的共
同的发展—安全问题,例如海盗、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境犯罪、环境管理和自
然资源开发等;在制度层面,区域内各种发展合作制度出现,推动域内各行为体间
的安全信任培养与互动,并催生新的安全互动与对话机制来保证发展;在文化方面,
发展—安全复合体整体上来讲是格劳秀斯文化主导的理性主义:国家间的利益既不
是完全的对立也不是纯粹的一致,而是一种博弈——一方面是分配性的,另一方面
也是生产性的。战争和国家间的其他冲突不再是最典型的国际行为,贸易,或者更
笼统地说,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交往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流。 在深度的发展—安
③
全复合体中,发展本身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复合体成员普遍认同的共识和价
值,进而改变了行为体对安全的传统认知。这一阶段,发展—安全联结更多的是和
谐积极的,发展不再是安全的依附者,而是成为影响区域体系的重要因素,发展—
安全联结通过各种发展合作表现出来,除了一般性的发展援助外,更为复杂的裁军、
体制改革、能力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国家重建等诸多内容也被囊括进来。
④
①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6, pp. 50-90.
②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3, 2000, p. 464.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25.
④ Mark Duffield, “The Liberal Wa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Security Impasse:
Exploring the Global Life-Chance Divide,” Security Dialogue, Vol. 41, No. 1, 2010, p. 58.
· 129 ·